「本土」不就是腳下的土地、眼前的城市嗎?但為甚麼有時候「本土」可以很遙遠,尋找「本土」可以很不容易?
如果說寫作是一種對自我的尋索,那麼,寫作人如何發現他跟一個地方的關係,就必然是其中的重要歷程。對於我——以至很多澳門人——來說,尋索本土的路是迂迴的。
我是澳門人,但在寫作上卻曾經有段長時間跟這個地方關係疏離。從2001年起,我在澳門一份報紙寫電影專欄。由於澳門沒有電影產業,只有零星的獨立製作,因此我的專欄也以外語片及中港台的華語片為主。曾經有四五年時間,我的文字裡面沒有澳門,而我也沒甚麼興趣要討論關於澳門的甚麼。
2005年秋天,我在英國開始了研究所生涯。最初,我鎖定以城市空間為切入點去研究華語電影,於是埋首閱讀城市社會學、後殖民空間、左派空間理論的相關書籍。然而,讀著讀著,我想到的竟然不是我準備研究的楊德昌王家衛,而是澳門——澳門舊區的歐洲式小城結構、不同城區的階級分野、天際線的權力隱喻、殖民時代地標的文化意涵等等。
英國的學校
英國的秋天日照時間越來越短。我常常在學校的圖書館興奮難抑地看書,偶爾掩卷思索關於澳門的種種,直到窗外天色轉暗。在澳門生活了那麼多年,我竟然到了地球的另一端遠距離看澳門,才發現很多我從來沒留意的事物。我當時自問:我為何很少把澳門當作一個嚴肅的問題去思考?
2006年初夏,澳門發生了一次轟動的五一遊行。其時,大型賭場進駐,大量遊客湧來,同時,社會問題叢生,市民怨氣升溫。當時Facebook尚未流行,我很多朋友透過MSN談論遊行,就連平常最不關心時事的朋友都主動傳來新聞圖片,問我知不知發生了「大件事」。過了幾天,寫專欄的澳門朋友紛紛撰文討論遊行,我頓感失落:首先,遠在英國,我不太清楚事情來龍去脈,難以成文,再者,我當時寫的是電影專欄呢。這事給我留下一個問號:我何時有機會好好討論澳門問題?
人生與寫作軌跡的轉變,往往就發生在下一個路口。2007年初,報章副刊改版,編輯邀我寫文化評論,提供一個寬廣得多的舞台:我可以跳出九百字的框框,突然有了三千字的篇幅,更重要的是我終於可以直接寫澳門。於是,我嘗試用我那幾年所學的去探索一些未被談論的澳門議題,例如五一遊行路線的階級隱喻、天際線的權力角力、本土小說的世界性、文化遺產的文化政治等等。事隔多年,從電影到英國繞了一大圈,我的文字才終於跟澳門本土相遇。
有趣的是,這不只是我的個人經歷,而是跟某種本土覺醒有莫大關係。一直以來,澳門又小又無影響力,長期在「中港台」的概念下隱形,在「港澳」的概念中被忽視,被認為「缺乏重要性與代表性」,因此,書寫澳門曾經是無足輕重的。當時,澳門人做論文很少會寫本土題材,很多人根本不覺得澳門題材有學術價值。後來,成為一個稅收超越拉斯維加斯的賭城之後,澳門既是風光,同時也曝露了很多深深淺淺的問題。然後,澳門終於變成了一個「問題」。曾經被認為沒甚麼好討論的澳門,突然成了談論熱點,一種本土覺醒也在社會問題、保育運動、懷舊照片中慢慢浮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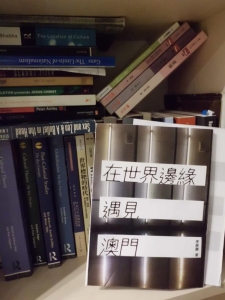 如是,幾年下來,我寫了好幾萬字關於澳門的文化評論,後來結集成《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一書,企圖重新認識這個被忽視的邊緣之城。當然,香港跟台灣也有某種政治與歷史上的邊陲性,但起碼這兩個地方的邊陲性是有被說明的。澳門則是邊緣外的邊緣,不只被外間無視,甚至被本地人漠視。
如是,幾年下來,我寫了好幾萬字關於澳門的文化評論,後來結集成《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一書,企圖重新認識這個被忽視的邊緣之城。當然,香港跟台灣也有某種政治與歷史上的邊陲性,但起碼這兩個地方的邊陲性是有被說明的。澳門則是邊緣外的邊緣,不只被外間無視,甚至被本地人漠視。
當我的文字接上了本土,近年網上評論平台的興起卻把這些文章帶到澳門以外的地方。兩年前開始,我為台灣香港大陸的好幾個網上平台供稿,某些關於澳門的、或是以澳門視角書寫的文章,竟也意外地得到一些關注(例如某篇談論澳門的城市空間如何被旅遊業粗暴地改變的文章,大概撃中了台灣朋友對旅遊業發展的擔憂,被很多網友傳閱)。原來,澳門問題有它的跨地域性,在這世代,我們都面對資本進出、人口流動、文化混雜等相似情況,而小小的澳門正是集中了這些普世現象。書寫澳門的同時,原來也可以書寫世界。
我的寫作經驗告訴我,本土是奇妙的東西。你以為本土議題一定近在咫尺?不,我們有時要經過一番覺醒才能看見本土。你以為身在本土一定最了解本土?不,我們有時需要地域距離與外來視野(如理論)去觀看本土,才能看得清楚。你又以為書寫本土就是封閉的、排外的?不,本土議題不是狹隘的,它有外延性及流動性格。而本土性與世界性,亦從不是對立的觀念。說到底,對本土的書寫,終極目的就是探索世界。
作者簡介:文化評論人,英國Sussex大學傳媒與文化研究博士,現任教於澳門大學傳播系,《新生代》雜誌總編輯,著有《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電影的一百種表情》等,編有《最後的蔓珠莎華:梅艷芳的演藝人生》。
照片提供:李展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