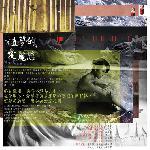作家西西在《哀掉乳房》中寫道︰「我們是在長期不斷的誤讀和重譯裡獲益。」
蘇珊‧桑塔格(1933 - 2004),美國作家、評論家,曾在南斯拉夫解體後在兵臨城下的薩拉熱窩與當地人排演《等待果陀》,在世時一直積極地把結構主義大師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理論引入到美國。
這次胡美寶、周可凡、楊振業等創作人嘗試大膽假設文本的可讀性,利用劇場符號來小心求證文本在劇場裡的詮釋意義,成功與否要留待觀眾自行判斷。到底入場後觀眾欣賞到的是一次忠於原著的演出,還是桑塔格的讀書報告?
不論演出結果如何,在創作過程中,創作人必然會面對兩個問題︰閱讀和翻譯。閱讀和翻譯固然包含了對字面意思的理解,同時也是個詮釋過程。符號的不穩定性為文本帶來多層閱讀,這是文本在作者身後仍然存在,而且還擁有生生不息的存在意義的原因所在。有人會因此而質疑,文本就這樣脫離作者意圖了嗎?這個也是胡美寶等人期望利用劇場來探討的問題︰「我們想像……文本的命運,是否註定被『斷章取義』地探討、詮釋、演繹? 」我們不妨參考一下Harold Bloom在著作《Anxiety of Influence》所提出的觀點︰
誤讀是種創造性的校正,實際上必然是種誤譯。一部成果斐然的詩的影響的歷史──亦即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詩歌的主要傳統──乃是一部焦慮和隨心所欲的修正歷史,是歪曲和誤解的歷史,是反常和隨心所欲的修正的歷史,而沒有這一切,現代詩歌本身根本不可能生存的。(Harold Bloom/徐文博譯,1989:31)
對於Bloom來說,誤讀是種創造力,這種創造力是源於一種焦慮,一種對前人創作的焦慮;為了克服焦慮,誤讀是必然的,而誤讀所帶來的就是新的創作。因此,詮釋不單是要為了理解作者/文本,更重要是為了跨越前人的成就,這是一種希望擺脫前人的陰影而建立自己的心理。擁有這種心態並不代表對前人不敬,純粹只是因為我們生活的世界,如羅蘭巴特所說,是個echo chamber,沒有全然的原創性,所有文本、創作均具有互文性 ,而《Alice in Bed》本身就是個擁有非常明顯文本互涉痕跡的作品。一切(現有的)創作、閱讀都是建基於(已有的)創作、閱讀;因此,無論創作人如何努力,最終演出不免都會淪為經「斷章取義」的《Alice in Bed》,而這次《Alice in Bed》的演出(事實上他們的劇目為《Alice Dreamiosis》),將會是一場處處得見前人陰魂,卻又擁有獨立生命力,懂得自我發聲的演出。
看罷排練,的而且確感到這群創作人的熱誠。從他們的演繹中可看得到他們對桑塔格的文本的確下了番功夫,但演出介紹開宗明義就說明這套可不是翻譯劇。這次《植夢的愛麗思》的演出在表現女性角色的困窘境況比原著要強得多,如果桑塔格寫一個劇本是要為了分析女性內在潛能的局限(詳見桑塔格原著劇本後的著作者言),胡美寶等人的劇場探索行動就具體地表現了這種局限到底會為女性的身體及心理帶來一個怎麼樣的狀態,換言之,就是利用各種劇場語言,把桑塔格的潛台詞解放出來。而值得我們去思考的是,當香港充斥著歇斯底里的女性主義劇場時,《植夢的愛麗思》似乎在提醒我們,活在都市的女性除了要為自己步入三十歲而大聲叫囂外,作為女性,我們到底還要關心什麼?另外,《植夢的愛麗思》裡所出現過的人物,不論是主角Alice James還是來開派對的白素貞、張愛玲等,她們都已成為歷史,到底這些人的故事,對於我們這班活在網絡世紀的女性又有什麼意義?這些問題,讓我留給觀眾去解答。
「超連結—牛棚實驗劇場節2009」評論人節前導賞文章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統籌。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