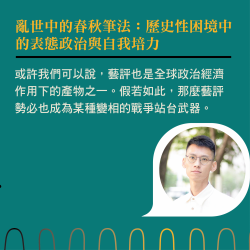2025年2月
當代藝術評論,總會在特定周期中被宣告頹萎、危機或死亡。
近年來,眾人對藝評失去信任的最大主因,不外乎是認為當代的藝評喪失了其「獨立性」與「批判性」。這一項認知的極大關鍵,在於原本位居生產鏈末端,以及作為評價和鑑賞藝術作品的藝評,已經更大程度地涉入到傳播生產線當中。在各種館舍、單位、機構網絡的串聯互通之下,藝評多被質疑跟媒體共謀產銷套路。此外,從生產鏈末端跳入到前端的藝評人,也陸續參與更多的評審、策展、機構行政等工作。這些在藝術生態圈中的另一種層面之生產行為,之所以受到眾人高度嚴苛的檢視,與其說是因為藝評自身的倫理典範與道德問題,不如說其實跟資源網絡的重新分配更加緊密相關。
藝評該如何適切地保有獨立性、自主性,以及害怕被媒體、機構網絡完整收編,從而引發廣泛性的倫理焦慮,都一再地左右著一般大眾對藝評的貞潔測試——無論是藝評長期作為一種獨立個體的思想工作,或是讀者對藝評人的人格判定。然而,更本質性的災難也因為藝評陷入上述「媒體化」、「機構網絡化」的生態循環迴圈,而使得自身必須一再順應文化生態與時髦趨勢下,而在論述上造就的詞句重組、話術遞歸。這般困境也必然使得思想工具長久缺乏創造性,無法回應瞬息萬變的世界格局,以及變幻莫測的政治動態。
不過,這些批判藝評的話語,從歷史性的視野來看,都不過是常態性發生的長期問題。事實上,如果真有甚麼現象會把藝評帶入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機,那麼更可怕的恐怕是——當代多極世界的立場分化與使命重構。
多極世界中的藝評:政治經濟作用下的價值觀
美東時間2月28日上午,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白宮會晤破局震驚全球。大家終於願意認清,世界政治格局其實不過一盤生意。當全球不再全球化,世界朝向多極發展——我們已然遁入不可逆的亂世之中,而且情況可能會隨著各國多極愈發膨脹的張力,而變得愈來愈不可收拾。
當代的藝評,早就從藝術品位的美醜判斷、高下之分這些討論作品內部的封閉範式中逸脫出來,而去擔負起更龐大的社會責任。從二十世紀戰後至今,我們反省過西方現代與後現代主義對藝評的箝制,從而展開去殖民的評論書寫。歷經過各種理論思潮與國族意識的快速更迭,藝術創作、評價與知識體系已然全面規格化的今時今日,地方性和區域風格特色再度成為新興政治發言。
不過,我們身處的亞洲,覺察到當代藝評的困境已跟全球局勢緊密掛鉤,以致於從文化生態到話語技術的塑形,都難逃當代世界變動和新冷戰的遺緒,以至於知識遺產的重新分配。因廣泛對西方自由世界的嚮往,我們從人權到人類世、微觀生物到宏大生態,無一不注入我們遲到但總算迎頭趕上的關注與愛。但在近年來,極右翼勢力的大勢擴張,所有本該被視為政治正確和不正確的價值觀,都一再受到顛覆與挑戰。
面臨左翼思想的疲態、「亞非拉」(編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與第三世界在新冷戰中成為知識分子的古早味鄉愁,「全球南方」也在第15屆卡塞爾文件展以後備受挑戰——我們對萬事萬物的愛,必須在經濟化的網絡之中相互交換、傳遞和給予。然而,所有現行的藝術術語,恐怕難以充分解釋非西方藝術實踐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也無法回應後進國家與地區的藝術家生存狀態、創作環境的現實。
當批判文化帝國主義成為笑話、政治正確變成髒話以後,「邊緣」、「滯後」、「弱勢」、「壓迫」等概念,逐漸淪為當代藝評的歷史參照與指認的前線工具,而非現實觀照的穿透與洞見。然而,所謂的亞洲、東南亞、第三世界、全球南方的創作者和藝術創作,在全球市場的需求下反覆現身的同時,卻又在全球市場供應飽和之後被排除在外。過往,藝評擔負著轉譯、代言、中介藝術作品的任務,傳達給下游的讀者理解、感知。如今,藝評在做著同樣的事,但更多的是為上游的機構網絡、市場生態、西方體系所服務、引介。
或許我們可以說,藝評也是全球政治經濟作用下的產物之一。假若如此,那麼藝評勢必也成為某種變相的戰爭站台武器。
激進的個體與被拋下的集體:差異世界中的知識懸殊
廿一世紀以後,全世界再也沒有宏大規模的知識運動,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次因應政治格局而零星發散的微小抗爭。更遑論2010年以降、自媒體的全面崛起——個人主義式的知識生產,多數的無名小卒可以開始透過藝評、劇評、影評來塑造自己的人設、個性與使命。新自由主義以降的個人,其身份政治以及國家主權都必然走向進一步的確立。無論是過去總是被視為弱勢或邊緣的族裔、語言、性別等,隨著個人意識的強化,推動了權益的爭取與「自我」的重新贖回。本土主義、國家主權是否得到重視,也關乎個體的自我肯認跟所在、所屬之地的緊密辯證。
如今數位媒介、社群媒體平台的無遠弗屆,以及身在更能自由表達的場域,個人能夠發揮所長、發表見地的機會和成效遠比昔日強大。AI時代到來以後,在ChatGPT和DeepSeek鬥個你死我活時,書寫機制和書寫的創造性本身變得輕如鴻毛。更重要的是,倍速社會下務求快狠準的表態、拉幫結派;從藝術喜好、美學品味、現象判斷,到對社會、政治的關懷與立場等,個人能夠付諸的表態愈勇愈好。愈是反省愈顯智慧、愈是批判愈有膽識——在「表態」成為一種當代的發言站位起手式、「反省」也變成了另一種嶄新的現代性,話語掌握發球權與控球權;立場先搶先贏、反省愈快愈精。
我們極力免除現代性的滯後時差——無論是透過網路資訊的通達,大至國家、小至民間的展演節目買辦,或是知識流通的無差別輸入與輸出。若回到十年前,要在當時的馬來西亞買到一本聽聞很久的書,只能寄望國內連鎖書店或年度大型書展;而今天只要在吉隆坡的誠品書店中,最新出爐的港、台出版品直接產地直送——過去仰賴的經銷書商,現在都被替換成巨大量體的經濟鏈,更遑論電商與網購的普及化,確保了群眾的知情權可以被更大程度地與海外縫合,知識差異彷彿就此得以被彌平。
然而,你與我終究並非活在同一個世界當中。縱使各式生態中的網絡、網狀關係被高度強調,或是其系統的交織性被眾人頌讚,但太快放棄對線性因果邏輯的探究和認識,只會成為對事件歷史化的迴避。雖然知識體系被各種網狀生態與經濟網絡給無差別、無阻滯地接駁,但來自不同世界的人們,所持有的感悟和認識論,就是會有資訊落差、認知感受差異和價值懸殊。這一方面,關乎同一種知識和資訊,在不同政治立場和社會角色的身分而質變,也注定影響著不同文化脈絡下的收受行為。於是,藝評的書寫強度、知識系譜,被不同地區的讀者所閱讀,就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收穫。換言之,一篇同樣的藝評,將會被讀成千萬種得著。
如果一位藝評人,或是一篇藝評是個激進的個體,那麼其讀者可能未必同其作者共享同一種理念、知識的交換。當這種因為知識體系所造成的根本性差異、分化,也就會有一群被時代、知識階級給拋下的集體讀者。藝評的使命可能會在其口耳傳播、理論旅行的路上,遭遇無意的誤讀,或是惡意的曲解。到頭來,藝評除了觀照藝術性、美學判斷以外,其所涉及的個人經驗與道德判準則,是否適用於更多人口的讀者,也就完全體現出讀者集體的歷史性困境。
戰國時代中的春秋筆法:藝評的生存與保全之道
在許多無法直白、暢所欲言的地方,一般上都是表態稀缺之地。同時間,所謂藝評的「獨立性」與「批判性」,在今天許多地方來說都是極為奢侈且難為的。
回首自身曾在馬來西亞的來歷,自是極其深諳言論的束縛、家國政治力的捆綁。無論是大至政治社會訴求、小至劇場觀演心得,那種言辭壓抑、不自在的感受,雖然可供三五好友在私下怨懟,但始終難以在公開場合攤開牌面。事實上無法全然自由這件事,並不會對實質上的日常生活與大小事有過多的干擾和影響;只要不囂張、不刻意針對、不鑼鼓張揚,基本上日子尚算能行。不過偶爾觸碰到本來就敏感的議題,多少還是需要謹慎言行便是。無可避免的自我審查總是先於機制審查,無法確切表態就先學會如何表達。說話和談論事物的尺度進退、方寸拿捏,久了就熟練、熟了便穩陣。
戰國時代比起春秋愈加混亂。很多時候的一時亂世就會亂足一世,外部世界的動盪常戰常有。不過,自我面對世界的策略,仍需持續更新和汰換,以應對隨時一觸即發的重大變化。前些日子讀畢青年學者李宇森的最新著作《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政治主體與國際主義》,作者以華人世界常言道的「如水」哲學,闡述離散群體的未來不能只是一種基於同國、同族的共同體,而是有可能擺脫舊有的身份代言,從而透過各自同異的敘事,重新建構流動的主體狀態。其中,他更提及「諸眾」(multitude)如何可能作為超越生命政治的民主實踐。全書立意良善,但讀著讀著,總是好奇倘若作者再過個二十年,是否還能如此樂觀看待?
「如水」確實是最佳理想,亦是上善之道。但在很多時候,現實情況始終要比願景來得更為複雜。因為在歷經離散敘事、歷史性困境、政治情態一波三折、社會共識永恆性動盪的地區,所有我們能理解的「抗爭」、「如水」、「變身」、「進入體制反體制」等各種名目上的彈性身段、韌性游離,往往是知易行難,而且還要比想像中更難。馬來西亞如是,世上許多地方或許也是。
當年自己因為祖國形同悶鍋,無法健康、自由地談論藝術,就借了個升學讀書的理由遠赴他國深造。如今,我得以在自由表態、表達的地方從事藝評工作。不過,這並沒有讓我覺得,自己可以從此告別那些艱難刻苦的地帶。時至今日,我仍然在考量一件事:如果有一天,我萬不得已,必須遁入一個跟我現時知識體系、語感模式完全差異的世界,我該如何繼續寫藝評?如何繼續毫不遲疑地表達與表態?這個差異世界,可能是回到我不再熟悉的馬來西亞,或是一個跟馬來西亞一樣不方便公然挑釁權力當局的地方。離開得愈久愈遠,是否也會漸漸喪失彈性進退的能力?於是,我彷若又必須重新開始複習自我培力(self-empowerment)的方法,以訓練自己永遠都要記得差異語言的表達方式與表態方法。這不僅僅是白話文與抽象表達的轉譯問題,更是一種如何尋找隱喻與象徵技藝的表態能力。
我偶爾不時會想起我鍾愛的電影導演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比起直接的社會表態、政治抨擊,他更擅長採取隱秘又幽微的影像美學,來道出深刻又雋永的個人立場與態度。決意離開泰國、前往哥倫比亞繼續拍片的他,交出的長片作品《記憶》(Memoria,2021)不僅證明了原鄉國籍身分參照陌異世界的可行性與潛力,更道出了縱使跨越了大半個地球,依然能在創作中持續舉重若輕、飽富現世批判,又將其予於寓言式包裹的高度美學能力。這除了是一種才華與天賦,更多時候是基於一種洞透自我的能力;唯有清晰自身的戰鬥位置,方能在各種世界中進退得宜。
我想,如果創作者能夠善用隱喻、象徵——此一屬於藝術與文學的獨到傳統,那麼藝評人的書寫,有沒有可能如此重建一種既具備美學鑑賞、社會表態之餘,又能以顧左右而言他、隱晦藏匿的話語,給予讀者拆解與領略?
古有云「春秋筆法」,既是善用華語文字自帶一語雙關、諧音異意、象形造字等奧妙 ,完成既不危言聳聽也不漠然輕放的表態與表達。「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莊子曾明言人的生命與時間有限,但知識與世界的無限滋生,使得我們容易體乏神傷。所謂順應萬事萬物的能力,大多時候仍然止步於一種近乎烏托邦的超凡想像,不過雖然我們沒有辦法真的上善若水,但隱喻與象徵是屬於文字寫作者、萬物書寫者的獨到技藝。在表態尚無法構成大幅度政治行動的地方,不時從中借鏡一種個人主義以外的集體生命聯結,以自我培力成尚存一絲彈性餘地的柔韌身段。又春又秋,絕對不淪為奉承或是犬儒;而是在歷經大破大立以後,懂得放下傲氣、剛硬與我執,試著去柔軟與卑微。留得青山在,也就認清自己的方寸之地;留一口氣,點一盞燈。
作為自由民主的「普世」概念,以及作為離散、受壓迫的「歷史特例」——身處於歷史性困境中的社會集體,雖然喪失了欲求所向的普世,但往往也從歷史特例中覓得新的絕技。書寫和言論的自由和民主化,並不能完全頌讚或怪罪自身所處的地方和處境,也無法一直寄望外部社會與環境來賜予。或許,我們更仰賴如何認清自我的限度,同時嘗試理解遙遠他人與他者,縱使是無法深刻同理也要感知彼此所困為何。如果我們曾有何種「不自在」的共同感受而有機會走在一起,那麼在不同的世界、差異的時空之中,必有彼岸的另一群人,時時刻刻提示著自己如何走出的每一步路,都是朝向良善的方向。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