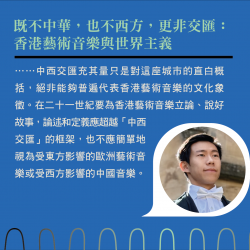2024年12月
長久而來,香港自我標籤或被標籤成「中西交匯」之地。官方愛此形容詞自不待言,且看尤其近年的施政報告。這詞用於樹立城市形象之政治用語或客觀之地理描述上,無可不可。藝術層面上,城中比比皆是的藝術創作和表演及其評論都以「中西交匯」自傲。但直接將表面、片面的城市印象直接形容其所代表的文化其實不妥。譬如一個在西亞或北非的「沙漠」城市,其文化特色難不成是沙漠?就創作、表演和評論而言,何謂「中」、「西」和「交匯」,也是極大的命題。況且世上「中西交匯」之城,含正方興未艾和已悄然退場的,不知凡幾;「中西交匯」本身就是個過於普遍的敘述。以此來細緻描述城中的文化、藝術,容易陷入「因為中西交匯是我城特色,所以我城藝術特色是中西交匯」膚淺的循環論證中。所以,不論從文義上或文化上,「中西交匯」一詞雖好,但不必每每把其跟城市的文化價值相扣。
我城的藝術,例如從音樂中,有無除約定俗成以外的思考角度?
英國作家Richard Hughes在1968年寫出著名的「借來的地方和時間」一語,形象地描述其時香港。這不確定感、缺歸屬感源於一個亟欲探討、表現身份意識的時代,「東西交匯」或「中西混合」,顯然是手到拿來的概念,是在一個困頓時代中特殊的魅力。
香港藝術音樂所謂的中西交匯特色,究其歷史背景,成於殖民地時期的較後期。重光後的這城迎來從戰後中國大陸遷來的作曲家和海外音樂院校學成歸來的土生土長音樂家,他們最大特點是相當傾向在西方音樂語言(器樂合奏和藝術歌曲等調性音樂)中或多或少的以文化符號(古詩、人物歷史、儀式、地點等)和標題音樂表現所謂中國元素。當然,其時身受傳統調性或其時席捲歐美之前衛音樂語言影響的創作者,有意或潛意識地要多少展現自己的華人性、文化的正當性,完全是能理解的,不過所中所西所交匯,其實很多基本與香港的本位無甚交集。
簡單將香港藝術音樂特點歸類為中西交匯,也有個明顯的盲點,就是並非所有從業者都服膺這標籤,以此為前設亦會有重要作品、人物無法定位。例如長期居港的英國作曲家紀大衛(David Gwilt),從七十年代起在港發表大量作品,包括為合唱與鋼琴而作的《Three Medieval Lyrics》(1988)及為雙小提琴與鋼琴而作的《Fantasy》(1994),從未關心過中西交匯這一概念。他在2020年作為「毫無疑問香港音樂界其中一位最具影響力人士」接受香港藝術發展局「口述歷史及資料保存計劃」訪問時,選了十餘首平生得意之作,當中未見怎樣能被「中西交匯」概念描述者。
紀大衛(David Gwilt)(照片來源:香港電台網頁)
因此,中西交匯充其量只是對這座城市的直白概括,絕非能夠普遍代表香港藝術音樂的文化象徵。在二十一世紀要為香港藝術音樂立論、說好故事,論述和定義應超越「中西交匯」的框架,也不應簡單地視為受東方影響的歐洲藝術音樂或受西方影響的中國音樂。
那到底要如何理解和梳理香港的藝術音樂?沒固定和唯一的答案,但世界主義是合適角度。簡單來說,音樂的世界主義是形容世上的音樂活動不是孤立而是互動的。學術界觀察到這過程尤其體現於受不同文化衝擊的大城市,如十九世紀時的維也納、布達佩斯等無不是東西(歐)交匯的國際化城市時,見到固有的文化如何整合吸收新者,從而形塑整個城市文化印象,甚至輸出有影響的創作。
其實近年香港作曲家在海外上演的作品已突破傳統中西交匯的標籤。例如陳慶恩的歌劇,儘管包含一些東方元素,如混合的器樂編制和源自中國現代文學的劇本,但作曲家的意圖至多是調和兩者之間的音樂元素,並不志於寫出中西交匯的音樂。《大同》(2015)、《鬼戀》(2018)都是在香港首演後不久於歐洲、台北由相同班底——多國藝術家組成的製作團隊和樂團再演,其中有熟悉歐洲歌劇製作的日裔導演,也有在港逾二十年、特別擅長詮釋現代音樂的澳州籍中提琴手。世界主義不是體現在多國籍,而是讓藝術音樂作為語言、文化、專長都迥異的團隊所共同理解和執行的音樂語彙。再如,為紀念香港大會堂六十周年,香港政府委託作曲家鄺展維創作管弦樂《緣起》(2022),由「倫敦愛樂樂團」首演,音樂也無從找到直接引用中國、香港元素的直描手法,而是使用零散的無調性片段擬人化地描繪大會堂一甲子滄海桑田的一瞬瞬。香港的音樂實踐者,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長期以來一直在回應與香港藝術音樂相關的某些刻板印象和誤解標籤。
左:陳慶恩;右:鄺展維
(攝影:[左]Mr So Photography、[右]andy.lam,照片來源:香港小交響樂團網頁)
素無從一粒沙中見宇宙的筆力,世界主義不可一概而論香港的藝術創作,但實能重新梳理前人創作的足跡,毋用拘泥於文化二元之分,亦覆蓋更多「中西交匯」這過於簡化、刻板的概念所未包含的面向。跳出「中西交匯」的框架,也讓人可直面「怎樣具體地要說出香港故事」的問題——這不是膚淺地創作全無定位的藝術,或花大錢請一大堆世界和內地藝團短時間内快閃密集式獻藝,然後就聲稱體現了城市中西匯萃的特色。在這向過去繁華招魂的時代,與其千篇一律說中西交匯,倒不如從世界視角來正視香港藝術音樂乃至其他藝術種類,或能觸類旁通地重新就所謂華洋雜處的文化定義,試釋「以英文書寫的香港文學」、「以全英文入詞的香港流行曲」、「以粵語演出的外文劇目」等,為本港創作者的地緣流動性、身份複雜性提供全新視角。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