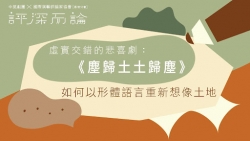《塵歸土土歸塵》
藝評人:盧宜敬、黎曜銘
主持:陳國慧
初稿整理:江祈穎
中英劇團新劇季的第二個作品《塵歸土土歸塵》,於8月在香港大會堂劇院順利公演。導演黃俊達帶領一眾中英駐團演員,以形體劇場結合集體編作的方式,重新演繹1993年的奇幻悲喜劇《咪放手!》。今集「評深而論」請來導演盧宜敬(Kingston)與編劇黎曜銘,還有主持陳國慧,三位藝評人從故事敘述、表演形式、服裝與空間的運用等多方面剖析劇作,更結合劇中情節,舉例解讀劇中符號的象征意義,帶領觀眾填補創作者留下的想像空間,體會解讀的樂趣。
以「土地」作元素,以形體作形式
故事講述善獸人在尋找土地途中遇到比較原始的畸星人,以及較文明高智慧的西裝人,西裝人把土地放在行李箱裡帶走,並遇到惡獸人,即是善獸人的另一面,兩個服飾差不多的演員,好像一個人的一體兩面。最後他見到幾個元首,元首把土地當成高爾夫球,將土地私有化。最後是善惡大戰,善贏了惡。作品重構自中英劇團經典《咪放手!》,以「土地」作元素,陳國慧認為45周年的劇目編排見中英傳承的意識,令舊作品能重演,並在其中找到聯繫當代社會的新元素,三位藝評人都未看過原作,只能想像,黎曜銘覺得《塵歸土土歸塵》延伸舊作「土地」之議題,重新構造了一個帶有神話色彩及象徵意味的新故事。
要用形體去處理這個複雜的故事,是一個大挑戰。Kingston認為導演黃俊達過往的作品,一直都以形體帶給觀眾衝擊,今次中英劇團的年輕演員能夠參與整個創作過程,是很難得的機會,而中英劇團一向以共集(ensemble)作為招徠,所以今次表演的形體訓練對演員相當重要。當中出現了不同的身體語彙,形體、默劇、小丑或弄臣(Bouffon)等等表演形式,雖然與圓融無阻地運用仍有一段距離,但演員嘗試挑戰及吸納,對他們往後的發展其他作品幫助甚大。但這些形式在本次演出中的運用似乎值得商榷,例如1993年的原作《咪放手!》,導演Gerry Flanagan是一個很有名的英國小丑老師,之前也曾經協助不同的香港劇場作品,引入以小丑作切入點的表演形式。但本次小丑的表演形式或形體語彙,似乎變成一種手段,用以區分不同人種,例如戴面具就是畸星人,又或者用非常有趣的服裝去做西裝人,是一些有趣的表演形式,但面具作為表演體系,未能以形態創造嶄新的形態特性,戴面具未能為人物賦予新角度去觀察世界,這點令人有所不滿足。
形態變化在一個相對複雜故事中,能幫助觀眾容易辨別角色,陳國慧認為演員如何適應這個演繹方式,又如何透過形體其他人種互動,讓觀眾信服他所演繹的角度,令人值得思考。例如當面具已覆蓋了面部表情,演員更需要用其他身體元素配合,令觀眾知道角色的內在感覺,又理解角色如何與其他人種互動,但這次演出令人意猶未盡。雖然演出前有很多不同工作坊,但要短時間適應這個純形體作品,對演員來說挑戰甚大,需要多一點時間來投入,才能找出幾種形體特性,使身體語彙能更突顯出來。黎曜銘受西裝人的有趣設置所吸引,西裝人整個人套上巨大的西裝,行動極度不便,令人聯想到異形中的破胸體,從胸口飛出頭說話然後收回去,沒有樣貌的身體如何活動以呈現其狀態?西裝人是在一個體制裏面被困,很想離開但沒有辦法,有點存在主義色彩那種不斷找尋卻無功而還的狀態。此劇有嘗試設置這狀態以令演員做到,而且顏色或身高都相當鮮明,或多或少令觀眾可以發掘出來。但陳國慧指出,設置後卻沒有足夠空間發展這個角色的特性,因為這設置限制了演員,這些限制會構成喜感,又能從中感到演員的內在悲情,而如何在短時間內進入狀態,對演員來說並不容易,演員如何利用這個限制發掘出身體美學,是值得團隊去深究的。
符號偏直白,語言欠轉折
《塵歸土土歸塵》舞台上符號相當多,但其深刻度與想像空間卻令人充滿疑問,Kingston認為故事線好像是三分鐘看完人類大歷史的一個濃縮精華,所以符號都嘗試用文明進程去歸納:由最初生命如何在土地孕育出來,開始群居,再衍生不同文明,到西裝人用他的服飾將自己裝得很高大,但其實內心根本狹小,然後用一些科技,例如槍,去奪取某一種權力,去批評土地是不是屬於我自己等。尾段刻意裝出大合唱形式,可解讀為世界大同的理念——萬物最後都會歸於塵土,一切變得空洞虛無。當中的符號傾向直接而淺白,從中建立的符號體系方向明確,所有片段朝著同一面向,一面倒的去看人的貪念如何令人紛爭不斷,就算未來鬥爭也繼續,這種人性的單一,符號亦未能深耕展開,難以滿足觀眾。
雖然以形體為主,但語言依然在此作品中有其角色。場刊相對詳細地寫出故事發展,開場曲也有簡單描述將會見到甚麼,到最後也有一些頗長的對白,令人很想一聽究竟,與純話劇對白大異其趣。黎曜銘認為語言運用符合人發展進程,前半描述比較原始的獨居或群居,是無語言的,直到出現文明社會,西裝人去總部開始有語言產生,而西裝人用槍殺死原始的畸星人,似乎能解讀成文明滅殺了原始的狀態,有如讀詩一樣的解讀樂趣出現,但這語言模糊犧牲了對人性的表達。Kingston亦認同這發展深具思考空間,中間轉折似乎參考圍城:「城內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同時亦聯想到香港人當下的狀態,因為官僚令雙方都未能如願,至死方休,另一方才能夠從中得益,這是文明社會產生的利益關係,但語言的出現太過理所當然,沒有其孕育過程。
表演具默契,嘲諷未夠盡
編作形式是《塵歸土土歸塵》運用的創作方法和手段,中英劇團過往亦很強調演員彼此的默契,1993年《咪放手 !》中李鎮洲、袁富華等,很著重以共集(ensemble)去帶動觀眾,無論是自己的能量發揮,以及怎樣講故事令觀眾產生共鳴,在短時間內要累積到一種默契很不容易,陳國慧認為今次默契雖然足夠,但結合小丑、特別戲服或比較誇張的形體方法下,能量發揮是有點參差,尤其捉不到劇情走向時,能量是有點鬆散,演員的身體語言交流亦較單薄,以使中間出現悶場。Kingston渴望能從面具或西裝等表演形式,看到鮮明角色出現,可以由其獨特視角看世界,而表演者亦由此眼光切入,以嘲笑某種情境或人性的醜陋面,但現時眼光似乎失焦而徒具形式,令這嘲諷未夠辛辣,在指出人性痛處上亦未夠到位。
黎曜銘亦覺得片段並非全部有效,例如畸星人死後同族人離開,而慘叫後任何人出場展現嘲諷,而總部一幕西裝人和善獸人及惡獸人不斷地錯摸,這種動作重覆亦較為有效。陳國慧指出黃俊達的作品中,重複是他常見的元素,這次亦見過往作品的痕跡,有策略地在同一個情景重複地發生,令觀眾多次進入處境,但有時侯會有怪異感,究竟重複是喜劇,還是不斷推石上山又跌下來的悲劇感?而當只有重複感而無劇情推進,就更只有成為悶場。Kingston認為重點在如何令整個演出團隊,在排練時對於這議題有一種很清晰而統一的焦點,這麼才能篩選出重心,從而對焦出荒謬之處並作嘲諷。但現時卻顯得隨意,任由演員演釋。故事是有更聚焦的必要,因為故事議題宏大,有關人類史上的貪婪與劣根性,人類如何爭取自己的利益並開向未來,這麼宏觀視點需要更精闢的視覺。
此外,表演運用較有喜感的小丑方式及形體動作,一開始似乎想帶給觀眾喜鬧的氣氛,但隨著事情發展,在極度喜劇的狀態進入一個悲情世界時,會有悲喜交集的感覺,陳國慧覺得前面的喜劇感未足夠,未能夠引導觀眾進入悲劇感。Kingston認為悲劇色彩是導演刻意淡化的,例如惡獸人的死亡是純粹意外,而任何人對畸星人的死亡都只是驚呼一下就完結,沒有任何英雄式的犧牲,令善惡變得兒戲,所有紛爭都只是玩泥沙一樣,從而展現人類的渺小。
舞台佈景象徵世界
作品没有很明顯的時間性,演員的裝扮亦似乎完全抽空了時間,而佈景以簡約白色來設計,透過不斷組合來推進劇情,這種空間的運用似乎大有潛力,尤其尾聲時有個半圓形的大布幕,製造了一個氣氛。其中在官僚體制裏,西裝人不斷申請離開,期間彈出很多佈景隱藏的物件,令Kingston留下深刻印象,就好像官僚手法不斷地延後這個人的申請,見到一個人的個人意志被官僚所磨蝕,雖然舞台運用並非絕妙,整個佈景處理所承載的意義與感覺似乎未夠準確,但他的確製造了很多可以走來走去的通道,提供足夠的調度空間以使用,那個看似月亮的半圓形布幕,能與外面的幾個石墩合起來,形成一個圓球體,似乎有意地作為地球意象的延伸,這些對世界的符號象微令人期待更多。
黎曜銘想到打高爾夫球一幕,幾條石墩一轉變成空心,用土地插一條桿變成小沙丘,扮演高爾夫球場,其實都有運用到佈景。整個場地下面有個半圓形的界及五個石墩,黎曜銘繼續探索解讀趣味,最喜歡最後一幕,降下一個圓形後,有一個戴單眼頭盔的尊者出來,坐輪椅且只能說話,不斷要求卻無人理會,走又走不到。眼在古代的象徵意義,有埃及的全知之眼,代表理念、智慧、判辨善惡,同時又象徵著一個殘缺的月亮,然後落下的布幕是否就是殘缺的月亮?他不斷唱一些大路歌曲如Imagine、What a Wonderful World,表現世界很美好,但風一吹來,一家人就全部走光,只剩他一個人。似乎亦在嘲諷那種宏大的善惡理念,其實都只如灰塵,一紙空談。陳國慧覺得這個太空人不斷說一些無意義的道理,卻又自身難保,有一種淒涼的意味出來,而月亮亦提升了悲情的意境。這些解讀難以判別真假,創作人有意留下空間,跟觀眾玩解讀遊戲,以引導思考與想像,亦是挺有趣的經驗。
作為中英劇團45週年一個的作品,觀眾未必知道《咪放手 !》,亦不知道以前的導演對劇團及香港劇場貢獻了多少,至少我們透過這個作品,可以再重新知道中英劇團的歷史,而亦受益於文獻庫資料,有助創作人能從中找到大量素材,重塑經典,讓其重新演釋,跟現代的我們,透過作品產生一個新的連繫。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