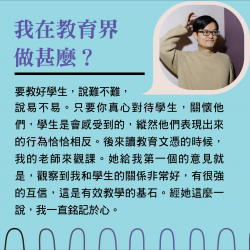 |
2024年5月
我最近接任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校長一職,有不少朋友頗感意外,為何我走進中學,忽然走進「教育界」?這十年認識我的朋友,可能只知道我在劇場的工作。其實我大學畢業不久便開始教書。不如就趁此機會,回憶一下我的教育之路。
我走進中學教英文,我的大學同學都頗感意外。我在大學時代做過電影學會、《學苑》(香港大學中文期刊)編輯。同學都以為我會進軍電影界。不過那時電影業一片蕭條,要找工作也不容易。我曾短暫地做過廣告公司撰稿員,厭倦了那種早上十時半返工,凌晨一點放工的殘酷循環。我記得有一段時間,疲累到走路也可以睡著。我又做了自由工作者一段時間,但剛剛畢業其實未有太強的人際網絡,大部分時間也是躲在家中看書看戲看武俠小說。後來朋友介紹我教「新來港學童適應課程」,主要教導剛剛從內地移居香港的小朋友英文課。最初我以為教書很沉悶,但在教學過程中真切感受到他們的天真爛漫。我很享受跟學生的互動,《新世紀福音戰士》就是他們介紹給我看的;也有同學跟我訴苦,說不喜歡香港的生活,因為住的地方遠比內地的小,奈何父母執意來港。
要教好學生,說難不難,說易不易。只要你真心對待學生,關懷他們,學生是會感受到的,縱然他們表現出來的行為恰恰相反。後來讀教育文憑的時候,我的老師來觀課。她給我第一個的意見就是,觀察到我和學生的關係非常好,有很強的互信,這是有效教學的基石。經她這麼一說,我一直銘記於心。剛開始教書時,我也模糊地覺得建立關係非常重要。建立關係也者,並非遷就學生。相反,如果老師只是一味投學生之所好,雙方的關係亦不會健康,學生亦不會成長。學生心底還是渴望老師的帶領及適當指導。
有了這次愉快的教學體驗,我決定踏進教育界。那時香港經濟不景,很多人想教書,我一直要到八月中才覓得教席。一間直資中學聘請我擔任英文、歷史老師。雖然是一間所謂的Band 3中學,但因為是女子中學,學生的行為表非常好。外界一般以為Band 3學生等於「曳」,但其實「Banding」是指小學學生升中的學業成績,並非指涉學生行為表現。我入中學之前不知道,原來我很喜歡當班主任。因為學生對我的信任,我可以和她們分享我關心的事情,例如國際關係。老師都要被觀課,如果安排的是自己擔任班主任的那一班,自然內心大定。喜歡教書的人不一定喜歡當班主任,但喜歡當班主任的一定喜歡教書。
左:香港兆基創意書院開放日2024;右:作者及其任教的香港浸會大學學生(照片由作者提供)
一個教育理論認為,最有效的教學,並不只教學科知識,還能牽涉其他範疇。我一直很欣賞考評局英文科出卷的同工,他們的考卷,往往涉及香港比較乏人討論、但國際社會卻在熱議的事情。多年後,一位舊生告訴我(她後來成為了出色的記者),我曾在英文課休息時間,播放陳綺貞的歌曲,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已經忘了這件事(最近在播YOASOBI)。我又改編《Lonely Planet》的文章,當成閱讀理解練習。我告訴學生,世界很大,歐洲也很值得遊玩及學習。A-Level考試後,只要做兩個月暑期工,儲到一點錢便可以去的了。歐遊不是夢!A Level放榜的時候,有幾個學生告訴我,她們真的歐遊回來了。
老師都要帶課外活動。我第一年教書被安排帶領田徑隊,還要在下課後到香港體育學院上田徑教練訓練班。我有長跑的習慣,但還是掌握不了田徑的理論知識。我第一年教書的時候,主任知道當時校長念茲在茲,想開托英文戲劇,於是慫恿我「搞」一齣。我膽粗粗接下這個案子,為畢業禮籌辦了一套英文戲劇。其中一個參與的學生,後來也成為了一名出色的記者。翌年,我申請帶領戲劇學會。因為要教學生相關的知識,除了當編劇、導演,我連SM(舞台監督)、DSM(執行舞台監督)都兼任過。我會找一個學生擔任相關職位,然後我再從旁協助。那時,我和學生做了不少編作劇場,有校內的,也有公演的。當中一些同學在江湖上重逢,也有些成為了我的同事,直到現在。
教書一年之後,我升任英文科主任,我覺得,不是我工作能力有多好,而是那時候沒有同事有空間、有意欲擔任此要務,而我又喜歡接受不同挑戰,從此,我踏上了中學的行政之路。後來這間直資中學申請了新校舍,開始招收男生並且擴班,由一間只有幾百人的中學,擴展至一千多名學生的學校。我也由原來的科主任升到首席主任,相當於一般學校的助理校長。行政工作是要換上另一種思維方式:講求精細、執行準確、組織能力、顧及大局、佈局、了解及協調不同人的想法等。這樣的思維,有時跟創作有分別,但我也很慶幸,在這段時間鍛鍊了管理、組織、溝通的知識及技巧,到我後來當上導演及營運自己的劇團的時候,有相當大的幫助。行政工作是為了令學校完成其使命,而不是因為方便行政而犧牲實踐使命的方向。這點我一直好好地記著,不論在藝術和教育工作亦如此。那段時間,我也看了一點管理學的書:Peter Drucker、管仲連的著作和《執行力》等,也獲益良多。這部分的經歷,我好像很少跟人提起。不是因為甚麼秘密,而是我覺得沒人感興趣,哈哈!
新校的歲月亦是另一段難忘的時光。校長是陳葒,就是那個放棄高薪厚職、去為基層「搞」免費補習社的傻瓜。有關學校的行政、管理經驗,我差不多都從他身上學到的。他不但會jump out of the box,而且說到做到。我常常跟其他人自豪地說,我師承陳葒(希望他不會介意)。有一年,視藝好友P推介我參加台灣高雄金甘蔗影展。主辦方橋仔頭文史協會,為入圍的參賽隊員提供住宿,而團隊必須在高雄於十天內拍攝一條十分鐘的短片。我校有影視科,我「心思思」想帶學生一試,但影展期間剛巧是學校的上課時間。我向陳葒提議,他二話不說立即支持。後來我校拍攝團隊真的入圍,經歷了一段難得、豐富而有趣的學習過程。
陳葒離校去追他的理想,之後兩年,我也意興闌珊離開原任教的學校。那時,我想花一兩年時間專心創作,再返回中學由低做起。其實我一直邊教書邊創作,其中有八年在《明報》「星期日生活」進行不同的創作實驗。我十分感激主編黎佩芬給我機會及空間。我也出版過繪本,舉辦過視覺藝術展覽。可是,如果要寫長一些、部頭大一些的作品,我覺得還是要多花一點時間。豈料,我一別中學多年,直到今天。這段時間,我也從沒放棄我喜歡的教書工作,繼續在大專院校教書,由毅進文憑課程到碩士都有教過。至於這段時期的劇場創作,我就不重複了。
有朋友擔心我當了校長會減少創作,答案當然是不會的。我一生人的事業只有兩個項目:藝術和教育。藝術和教育都在詰問人是甚麼?人類社會需要甚麼?理想的人及人類文明應該長甚麼樣子?我慶幸一直都在做自己喜歡而且有意義的事,我也希望每個人能盡展所長。這是人類社會公義的基石。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