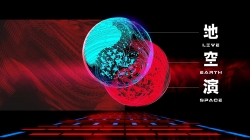 |
對談:蔡世豪(蔡)、馮國基(馮)
主持:陳國慧
文字整理:江祈穎
蔡:
今次為新視野藝術節做節目,由籌備到演出只有半年時間,所以只能選擇上演新曲加精選。疫情期間,我累積了一堆沒有機會用表演方式去發表的作品。例如去年大館委約的《MART》,名字翻轉即是電車的英文(tram),吻合作品以反向的視像呈現電車中環段的沿途景物;《Critical Era》則是以1880年至2020年的天氣數據而做的一個視聽作品,以及《Power》。節目也會包括與江記合作的作品,除了《一場幻覺》,還有《離幻時代》(2018)。另外我亦會做一個新作品,它將會是下年我在北角油街展覽的部分展品。
作為電子音樂人,作品只被展覽或放映而沒有在劇場裡呈現,雖然我並不覺得可惜,但演出的現場感及觀眾的即時反應亦同樣重要。上一次演出已是2018年的西九自由約,之後就是這次的《地.空.演》,也可以說是九年前《星.音.演》的延續。
馮:
與世豪的經驗相反,我較專心在劇場之上,所有參與、創作,無論台前或幕後,都在劇場的空間裡。剛才的分享令我想起,現世代似乎會在一個藝術範疇中提取一些個別元素,然後探索其在其他場合重新發酵的可能性,再不斷重新運用。例如取出某表演的燈光,再探索其單獨呈現的意義。這可能是新媒體的特性。
蔡:
雖然我主力做全新創作,但有時也需要平衡一下,就像創作歌手有時也會翻唱其他人的作品。重製只有在我與江記的合作中發生,他讓我重新剪接《離騷幻覺》的素材,然後我為這個作品創作新歌,所以重製只集中在影像上。我過往的作品很常呈現香港的城市景觀,而江記的畫中也有很多香港景觀,如果用蔡世豪的手法處理江記畫中的城市景觀,可能會碰撞出新火花。除了城市景觀外,我的作品裡還有太空宇宙相關的主題,相加起來,較有意義的敘事就是由地球演到太空,所以叫做《地.空.演》。
馮:
我覺得重製是一件關於整理自己的事情,做舞台重製時會面對不同空間,表演都不會一樣,會用自身的美感經驗,重新再作嘗試,以身體或光線去演繹其與空間或音樂節奏的關係。幸運的話,會有機會不斷「重製」,即不斷重遇同一個劇團、劇作家或導演的風格。但香港舞台缺乏重製,其實即是欠缺整理,大家都很抗拒重複,如能把這種重遇放回表演之中,對製作來說是一種很好的養分,能令作品產生更深厚的演繹。
蔡:
疫情下表演藝術界真的很困難,而其實在疫情前電子音樂人也愈來愈難單靠表演或銷售唱片維生。因此我在表演以外也探索其他可能性,例如展覽或非演出創作,並與不同界別合作,令自己能被更多鮮有接觸電子音樂的人認識,與我合作的人亦會被電子音樂界認識。
通常文學、舞蹈界別在看了我的作品後,覺得當中有些元素合適,便找我合作,例如與香港舞蹈團《風雲》、《中華英雄》的合作,是覺得電子音樂可配合打鬥場面。另外,也斯離世後香港藝術節為他籌備了一場音樂會,我選了三首他的詩作做成影像音樂,每首的處理手法也不同。與不同界別合作,多看其他範疇的作品也會對自己的製作有幫助。
馮:
最近我創作了兩個作品,一個是聲蜚合唱節委約我為一段古典人聲音樂,製作一條短片,與這段音樂溝通,另一個是九十年代香港原創舞台劇本再探索的影像短片。製作前我會思考我想在作品裡講述一個怎樣的小故事,故事會與影片的核心主題產生火花,又或把影像隨機排列再組合重構,然後相信自己的藝術直覺。這種直覺其實是來自生活,又或一些重複在腦海中出現的念頭,慢慢與主題或連帶字眼扣上關係。這個過程會反反覆覆,不斷重構,在字眼中摸出理路。但我尤其在做一些小型的重製作品時,會有很強烈的孤獨感,並有時不自覺把孤獨感放進作品之中。
蔡:
我已習慣創作的孤獨感,甚至覺得創作時需要一定程度的孤獨,需要一個人靜下來。電子音樂常常一人完成整個作品,有電腦就能製作出來。但自己創作時令我覺得很自由,我不需要去理會甚麼,而合作時我或多或少要顧慮對方的創作空間,這兩種狀態我覺得需要平衡。另一方面要視乎藝術媒介,近年除了影音作品外,亦有藝術裝置,一定要與有技術的人或團體合作。今次的《地.空.演》也不可能一個人完成,要有很多單位配合才能做到,人力物力心力極大。
電子音樂在外國流行已久,並已成為很多人看的商業項目,但在香港還未具商業價值。互聯網的興起,對推廣電子音樂幫助很大,現在可以經社交媒體或YouTube推廣。例如根據也斯作品創作的《寒夜.電車廠》更是我眾多YouTube影片中最多觀看次數的。而近年香港也較重視藝術,有很多活動、展覽發生,但城市生活節奏急速,這個時代的藝術家要在如此激烈競爭下能突圍而出,是相當需要技巧的。加上香港市場小,也要思考如何擴展觀眾群、如何持續地做下去。我會很願意與不同界別或商業機構合作,如Clockenflap、Sónar Hong Kong電子音樂節、香港藝術節或新視野藝術節,可接觸到很多層面的人。
馮:
疫情真的打散了很多藝術家的生存模式,無論哪個藝術範疇的人都要靜下來思考如何持續。我也在思考,甚至觀察到已有人在行動,例如策展人會把項目分拆,且更頻繁地展示,甚至收藏在不同角落,使藝術在疫情、空間限制下仍然能發生。這可能是以後的一個趨勢,他們會把作品再解構,或再組合不同形式的範疇,產生一種另類的形態,讓觀眾發現原來可以這樣觀察不同元素。另外,香港缺乏一些讓藝術發生的地方,不只是正規場地,而是當空間不斷變動,有沒有特別的方法可以聚集人群,令他們看到作品的存在,這方面可能會與互聯網連結起來。第三是觀眾擁有更多參與方式的選擇,可以在現場看,或在家中上網看,再引伸至思考如何創作新媒體作品。
蔡:
說起觀眾,我有個作品發射至GJ273b星球,到2030年就會抵達。事源Sónar廣邀世界各地音樂人做一段十秒的8位元音樂,我把《Signals》改成8位元版本並獲選,最後聯合其他著名音樂人的作品,透過歐洲衛星傳送往外星。我估計沒事會發生,若然高智慧生物有相應科技又與我們聯繫,可以接觸到他們也可能是十多年後的事了。
馮:
我是被衛斯理小說養大的,所以我相信外星人藏在木炭與眼睛之中。我想起在日本看過一個展覽,觀展的人可以寫下願望,負責人再寄出去,然後我們靜待回音。這樣與未知的地方聯繫,其實是在閱讀自己的情緒,思考我的意念在哪裡,可能跟世豪傳送作品到太空有點相近。
蔡:
近來愈來愈多關於UFO的片段公開,其實可能非地球觀眾一直在監察我們。雖然是半打趣說,但這些都開放給大家去想像。可見想像有多重要,啟發人類的發展,對藝術更是不可或缺。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