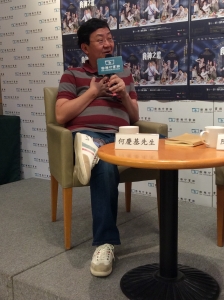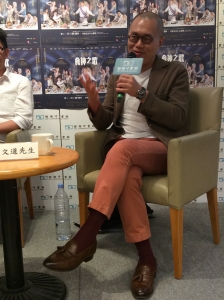整理:羅穎妍
日期:2014 年 8 月 31 日(日)
時間:下午 5 至 7 時
地點: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
主持:馮程程(「前進進戲劇工作坊」駐團導演)
講者:梁文道(文化評論人)、何慶基(資深策展人、文化評論人)、陳炳釗(「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藝術總監)
整理:羅穎妍
照片提供: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馮程程:
這幾位老朋友將和我們談談食、後殖民、九七,以及也斯的文學……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1997年的那一天,你們在做甚麼呢?」當時他們都在文化藝術圈中擔當重要崗位,趁著今天讓他們回顧一下,也讓我們知道當時的社會、文藝界氣氛到底如何。這個「回望九七」的動作,對於今天的他們來說,距離是遠或近?也斯的作品如何捕捉後殖民這個時段的香港的人與情?以上話題,希望三位嘉賓暢所欲言跟我們分享。
回歸當天無所事事
陳炳釗:
我們一見面就談起,當年香港藝術中心那個九七回歸派對發生了甚麼事,我想那個派對頗能反映當時文藝圈的狀況。但先不說那派對,我想說我在1997年做了甚麼。那年年頭我辭職了,離開「中英劇團」和「沙磚上」,後者是一個在1989年開始搞的實驗劇團,心態是想重新開始。
由九十年代一直走到九七,心境有點古怪,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我做了兩個決定:第一是讓自己回到自由身,第二是接受了藝術中心委約,在九七前後創作《飛吧!臨流鳥,飛吧!》。那個戲刻意在1997年6月28日於麥高利小劇場做試演,然後大概在九七回歸一星期後正式演出,我的心態就像做一個儀式,是我和一班劇場朋友的回歸和過渡。特意這樣安排,是因為覺得九七一定會有事發生,我要在試演時做一些事,沒有結局的,體驗過九七那幾天以後,才再做這個演出。當時我整個生活時間表的上半年就是這樣安排,因為演出是向九七進發,4、5、6月整個時間表都是朝著九七。
當時我跟藝術中心關係密切,有個叫「香港三世書」的策展,是藝術中心一系列跟九七有關的節目之一,我創作《飛吧!臨流鳥,飛吧!》,還有莫昭如的《吳仲賢的故事》,另一個是《阿佬正傳》,講的都是香港本土。那時進出藝術中心,不時見到視覺藝術家在創作,大家(的意念)撞來撞去。梁文道告訴我哪個視覺藝術家在做甚麼去回應九七,我覺得他們的「盧亭」意念挺好,那我就做臨流鳥吧!他們是魚,我是雀。大家互動著關於九七回歸的符號,在那個氛圍裡邁向九七。另外還有視覺的記憶。臨近5、6月我在藝術中心排練,每天從中環乘巴士到中心,到夏愨道上天橋時見到添馬艦,遙望會議展覽中心,看到那個回歸儀式的看台,還有趕建中的會展,每天經過看著都多建一點,有種絞刑架慢慢起好的行刑感覺。這感覺很深刻。
我和梁、何有些感覺很相似,就是九七當天無所事事。6月30日那天,所有朝著這點的論述都講了好多,真真正正那天來臨時,又還原了實實質質的一天,一個好難解讀的狀態,那天好像癱瘓了,無事可做。那天藝術中心在畫廊搞了個派對,畫廊外面有個小露台,斜斜對著會展,可以見到煙花。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看到很多CNN、BBC等外國通訊社攝影隊的擺陣,那個感覺很exotic(異國情調)。
那晚的派對我不完全記得發生了甚麼事。何慶基說心情很沉重,但我印象模模糊糊,不覺開心或不開心,想走又不知往哪裡去,外面播著交接儀式,電視台有娛樂圈各界慶回歸的演出,有好多奇怪的人來來去去。派對完了,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有人提議去立法局,那時在皇后像廣場有個另類慶回歸,長毛和泛民在發表宣言,我好像也有去那邊。後來部分人去了中環,部分來了我家開派對。第二天下大雨,大概大家都有這個記憶。那個藝術中心派對大概是羅生門吧。
香港歷史怎樣講?
如果說九七前較為強烈的經驗,文化上,真的跟也斯拉上關係。我和也斯都關注香港的文化身分和特色,一直覺得社會對香港文化很不公平,動不動就說文化沙漠。我們努力嘗試重新讓香港人知道我們也有鮮明、強烈、有趣的文化,大家的角度很類似,香港文化就在流行文化、生活文化當中。
我集中視藝的策展,每年搞兩個香港文化系列,集中展出視覺藝術的文化成就。當時有種心態:回歸前我們要確立自己的身分,為自己定位,因為我們正要面對強而有力的大中華文化,這種文化進入後我們會消失。當時民間出版了很多書,坊間很多聲音講香港文化,有趣的是北京方面也請了學者來研究香港歷史,這個混亂場面煞是有趣。當時我策劃的有關九七的展覽,文化圈對話很密切,文學和劇場都有,現在則很少這種對話。
我關注歷史本身的演繹、權力,作為策展人,當時最大的挑戰是1997年6月30日搞甚麼展覽,有甚麼想法要表達。有人跟我說,國內有個少數民族,其文化已全消失,但因為國家要推動文化旅遊,有人便虛構了那個民族的文化,包括婚禮、喪禮。香港人很「百厭」,喜歡作弄人,和我合作的藝術家很喜歡這個「虛構」意念,董啟章當時亦有份參加,於是一起搞了個展覽,就是「香港三世書」的展覽部分。
這是文化界自行有機撮合的藝術活動,現在回看,香港再也沒有這回事了。「香港三世書」分為三部分:歷史、社群、個人。歷史講「盧亭」;社群原本想搞個時間囊,讓人放「五十年後想給香港人看的東西」進去,五十年後再掘出來看看放了甚麼。當時陸恭惠、劉慧卿、達明一派等都放了東西,很多都是好個人的東西;另一個就是個人,我們找藝術家去深水埗訪問老人家,講回歸都是中產階級、商人發聲,從來沒有人過問窮人怎看九七。當時活動核心是「歷史」,1997年大嶼山村曾經有一次大屠殺,歷史上鮮有提及,換句話說1997就是大嶼山大屠殺八百周年,當然沒有人提及。歷史的選擇、虛構是很恐怖的。
建構歷史的權力總是在中央或學者手上,當時策展「盧亭」,是一個關於香港的隱喻,展覽開幕的第一句就是「我們從海洋而來」,而不是從大陸而來,當時有個叫《河殤》的電視節目,講海洋文化陸地文化,可見當時有很強烈的本土文化身分塑造,同時挑戰已經存在、和即將來臨的權威。6月30日當晚,我在大東電報局(編按:當時已重組為香港電訊)做一個BBC的現場訪問,接著就去藝術中心。文化界來了很多朋友,印象最深的是大家突然自發唱歌,那首歌是阿釗寫的。
陳炳釗:
歌詞只有幾句,但我都不太記得了,只記得開頭是「慶回歸,慶你條命;賀回歸,賀我反艇」,那首歌是《飛吧!臨流鳥,飛吧!》的創作團隊想出來的,在試演裡玩過,但到正式演出卻沒有。心境上我們都覺得這是宣洩式的東西,在正式演出中無從插入,但也好想做,所以試演時唱了,在派對上也應邀去唱了,大家好開心伴著結他去唱,心境上好像得到了某些治療。
何慶基:
我的心境是很複雜的,大家走在一起唱歌,有在一起的感覺是好的,而那首歌有些百厭,但那一晚是沉重的。對於整個九七回歸,我的感覺有兩面:一方面我開心,慶幸這個令人恥辱的殖民地歷史終於完結;另一方面又擔心面對另一個強大的制度。我最記得當晚我沒有再去派對,當時我在幫《信報》畫一系列漫畫,我回家畫完最後一幅寄出去翌日登,那幅漫畫說的是解放軍坦克車進場了。現在隔了這麼久,不幸地,真的可能發生。
「好忙的」香港回歸論述
梁文道:
我們講的事情,都是以灣仔藝術中心為核心擴展出來的很小部分,這是我們時空歷史的限制。不知道是否我的記憶有偏差,但我真的覺得當時大部分香港文化界都參與了那個小小的範圍,而且出現了一些何慶基口中好有趣的互動。整個藝術中心在做的計劃,放在這個大背景,其實是甚麼呢?
回歸前一兩年,香港變成全世界的熱門話題,全世界媒體都在看香港九七回歸是甚麼一回事,歷史上從未聽過這樣一件事,一個如此重要的殖民地,變成另一個國家的金龍吐珠,那是甚麼來的?所以很多人關心,學術界、文化界、藝術界都好多人在講。所以那年香港各行各業都好紅,我記得當年大家好忙,有好多來自全世界的邀請。我們有好多藝術家出埠,去好多地方做展覽,好多學者忽然變得熱門,每份學刊、特刊都要弄份香港特刊,從經濟到社會到政治到文化研究到文學都有,所以大家忙到不得了。我對九七最深刻的印象是,大家都好忙,忙著說九七是甚麼,香港是甚麼。現在回看,原來講了一大堆,仍不知道是甚麼。
香港是我們主場,主場總要做些東西,在1995、1996年已開始做。也斯有一本很重要的書是藝術中心出版的,叫《香港文化》,討論香港故事為何難講。這本書很重要,因為市面上從未見過一本書以香港文化為本位,所以在文化研究是頗創先河的。那本書以後,周蕾出了一系列的書講香港文化,當時學術界如葉蔭聰、羅永生、孔誥鋒等引發了一些討論,針對也斯和周蕾是中產階級資本主義、大香港主義之類,好熱鬧的。但當時算是很健康的討論,沒有現在這麼分裂,意識形態沒對立得那麼厲害,當時文化界、學術界大致上仍可以同桌而坐,縱使大家知道各自立場南轅北轍,仍可一起討論。九七時,大家第一次跨行業、跨科地討論本土。
當時我不是在藝術中心上班,但我弄到自己好像在那裡上班一樣。為甚麼天天去?因為我專門幫大家做跑腿:何慶基搞展覽,歷史學者、人類學家聚在一起討論如何做展覽,我就去幫忙;另外我是陳炳釗的戲的戲劇顧問;電影部當時是蔡甘銓做總監,我則幫忙做那時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IFVA)的評判,大部分作品都是講九七。巧合地有班經常去藝術中心的人,手上都有自己的計劃,例如董啟章,當時他正在寫《V城繁勝錄》,他一邊寫我一邊給意見。當時大家在做些事情,我就在中間跑來跑去,介紹大家認識,一起做些東西,這種跨行業的互動,好神奇。「盧亭」展覽後的研討會,甚麼人都有來,有一節有陶傑做主持!現在大家好難想像陶傑會去這樣一個展覽,跟大家講歷史與虛構,都幾好笑。
不約而同探索考古意象
我想說的是,陳炳釗的戲、「盧亭」展覽、董啟章的《V城繁勝錄》,都出現了共同意象,就是考古。大家面對回歸,似乎不太知道應該用甚麼尺度來掌握、量度此事,所以採取了一個科幻一點的角度,跳到好遠,把今時此刻當成陳年往事,要考古尋回這是甚麼。我覺得這態度好得意,就像身處於世界末日。八十年代我們開始講九七大限,當這天真的到來,無人知道眼前這事怎麼搞,於是大家採取的態度就是在時間上拉遠距離,去回想以前的事。
那時我們的展覽是從現在虛構過去,當時整個展覽都是「老作」。我在展覽有個小小貢獻,寫了幾篇文,說在香港大學圖書館的報紙堆裡,找回歷史上文人關於香港的寫作,是未曾發表過的遺稿。許地山、張愛玲未曾發表過的講香港的文章,都給我找回來放在展覽裡,但其實是我學他們寫的。當時李歐梵到來,覺得是好大發現,我就說其實是我寫的,我真的學得神似。
香港是甚麼,不知從何說起,似乎只能虛構。當時大陸講香港回歸就有套主流歷史:我們從前是小漁村,現在是個繁華國際大都會,失散了一百五十年,現在終於回到祖國媽媽的懷抱。大家一聽就嘔心,於是都想做些反抗,但如何反抗呢?好像不知道拿甚麼出來講。那時開始講本土,但本土是甚麼?大家有好多想像、虛構、疑問,但更多是解構。就好像《臨流鳥》裡面,甚麼是真實的香港?例如煮一碗粥,甚麼才是一碗真正的潮州粥?當潮州人把粥煮得糊糊的成了廣東粥,怎算潮州人?很多這類討論。董啟章那本書亦在解構香港,想講很多事情但不知從何說起。很記得陳錦樂的得獎短片《沒有人在(跑馬地)等沒有人》,講跑馬地墳場、大火、到現在的快活谷,整個歷史飄飄浮浮,很詩意很美,但不實在,好像講不出那是甚麼。
無能為力的預視
梁文道:
藝術中心畫廊的回歸派對氣氛好古怪,大家都覺得「今晚有啲嘢喇」,見證歷史時刻,我們都是最後一代殖民地被統治者。如何慶基所說,當時跟現在不同,現在很多人懷念英殖,但那時我們多數人不會這樣想。可能我們年紀夠大,知道英國佬的壞,但另一個要來的是否就是好東西?大家都見過六四。香港在中間就像一個給拋來拋去的球,完全無能為力,我們唯一可以講的就是些虛構的故事。那晚派對似乎應該開開心心,唱唱歌,有些表演。那晚我們一起看了鮑靄倫拍的錄像,大家聊聊天唱唱歌,接著聽到外面放煙花,就大叫「好嘢」,但是在歡呼還是喝倒采,很難分得出,其實亦是我們的心情。
派對結束後大家覺得好像不應該這樣過,應該再有些事情發生。我們有一班人走路去了皇后像廣場,當時廣場有個另類回歸活動,是文思慧他們做的,社運界朋友的活動剛完,就輪到港英時期最後一屆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他們坐不到直通車要集體辭職,就在舊立法會大樓二樓露台發宣言。我記得當時社運界朋友好恨他們,當時搞社運的人覺得泛民演員都是建制一部分,我們可是要再激進一點。但當時不少人支持他們,但其實結束了都沒甚麼事發生。回歸當晚最開心就是蘭桂坊那班鬼佬,無事可做喝醉酒,當晚有人被打爆頭送入醫院,香港離開殖民地歷史的當晚,就只有鬼佬在蘭桂坊喝醉酒出事,所以其實九七那晚甚麼事都沒有發生。
那晚我和幾個人在蘭桂坊六四吧通宵喝酒,天亮收到警察電話。那時我和胡恩威合作印了十萬張貼紙,其中一款用簡筆字寫著「同胞勿近」,好像六七暴動時那樣,從六月底開始到處貼。實是開個小小玩笑,香港要回歸中國,就告訴北面的人「同胞別過來」,但另一方面又好像善意提醒你,這裡有「土製菠蘿」,小心點,意思好含混。我們貼到出事,警察打電話來問,但當時警察不像現在,現在的話我該要坐牢了,他們問一問,「啊,藝術家!好吧別這樣了,別弄污地方啦。」當時警察容易說話,說兩句就沒事了。第二天睡醒,看著車入城,就結束了,無無謂謂,好虛無地完成見證歷史結束。何慶基剛才說的那種悲傷,我覺得是種更深層的東西,當時彷彿已經可以預見到今日,但又講不出是否真的會這樣,模模糊糊。
香港人身分的多元尋索
陳炳釗:
在九七階段創作的人,例如董啟章和我,對於虛擬歷史彷彿好著迷。當時我不認識董啟章,九七之後藝術中心連繫我們合作,才發現他寫的某些虛擬歷史角度,跟我自己1996年開始做的香港歷史、《臨流鳥》很接近。後來回看可能不單止我們,那段時期大家對虛擬和歷史的想法,都有某個脈絡。
「臨流鳥」系列由我九十年代初做《信報》記者時醞釀。開埠以來好多外國官員、政務官參與香港考古歷史,他們沒事做行山,業餘嗜好通常就是考古,記下了好多考古據點,但之後通常都沒有資源挖掘,所以儲了數百個歷史遺址,臨近九七就要處理,特別是赤鱲角機場那邊。當時我從記者的角度觀察到有兩個陣營,一是由外國人領頭的香港大學考古隊,另一是跟國內中央考古隊合作的中文大學。中大強調河殤文化,認為香港文化源遠流長之類;而港大就相對較開放,傳而不論,未知道香港文化源頭,更可能是一種割裂式的文化,受東南亞文化影響,香港族裔可能完全跟中原割裂,那時就有這些爭論。
這些爭論反映在一般藝術文化創作,八十年代初開始有一種「我是香港人」的意識,開始問身分的問題,這個問題朝著九七開始有變化。但似乎在主流的狀態裡,不斷強調一種論述:香港由小漁村變到今天,香港文化就是一種拼搏精神,所以我們要以香港為家,要覺得驕傲,這種論述不斷強化,雖然沒有強調龍的傳人,但強調「拼搏精神」其實頗單一,但又好像好有本土意識。
正如梁文道所說,我們由九十年代開始就在探討本土意識,我覺得新一代創作人都想做一種逆反思維,抗衡「我是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抗衡一種我覺得是假設性的問題——「國際交流活動裡,每個人都唱一首歌代表自己來的地方,輪到我的時候,想不到應該唱甚麼歌」——杜國威的《我係香港人》就是用這個意象去講一個故事,可能就變成要唱《在那遙遠的地方》那類歌。我覺得這種處境是個假設性、誤導式的問題,未必需要一首所謂代表香港的歌。那個階段我們都在抗衡那種單一論述,我們的思維就是去問,如果所謂香港人身分不是一個單一答案,有沒有可能?所謂香港人身分是流動的,不同階段我們對香港的理解都不同。九七階段那種流動性好強烈,雖然覺得要建構一種香港身分,但我們沒有試圖去排除某些東西,沒有排除英國人對香港的影響,沒有排除地說我們不是中國人,亦都沒有強調香港人一定要有某種拼搏精神,大家都在找一種開放的狀態。
尋找開放的探索狀態
最開放的狀態、最挑釁單一論述的,就是一種虛擬故事,於是大家就開始玩一種虛擬性,用不同角度去挑戰單一性。很多創作人的共同戰鬥對象是接近的,大家用不同策略去面對九七,其實都相當一致,只是方法不同。如用小敘事抗衡大敘事,「進念」當時在做《中國旅程》,問的好像是一些大論述,但又離開中國官方那一套;林奕華在做《兒女英雄傳》,轉向教育劇場,用年輕一代角度挑戰權威;潘惠森做他的「昆蟲系列」,刻意跳出來講香港式昆蟲如何生存。莫昭如則做《吳仲賢的故事》,和playback theatre(一人一故事劇場)有關,這形式傳入香港,其實跟九七那種狀態 很有關係。除了莫昭如那套民眾革命的論述外,一人一故事劇場亦再三強調回歸個體,應該如何聽民眾的聲音。
那時幾乎所有我認識的創作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抗衡單一,回應「香港由小漁村變成大都市,現在回歸祖國,期待更美好的將來」,我們用不同方法抗衡這種論述,某程度上各方面的聲音都團結。然而當時有種大恐懼,讓我們在團結的狀態下都不能做到甚麼,沒人知道之後怎樣,有種力量去到沸點。九七後有幾年時間,有種停滯的狀態,大家不知道要做些甚麼,差不多到2003年才有些新東西出現,中間好像空白了。九七挖掘了這麼多東西,九七後卻承接不到,有種斷裂。當時不覺,現在回看,其實九七是一種斷裂。
何慶基:
面對中共建構的文化身分,我覺得我的工作就是要建立香港的文化身分,但從哪裡找?歷史是最方便的途徑,像「盧亭」,我們虛構歷史,挑戰歷史的權威。為甚麼只有學者可以演繹歷史?我們要把權力拉回來。歷史可否是一個隱喻?盧亭對我來說是種半人半魚,介乎兩者之間,逃難而來,這些全是屬於香港的。我記得當時大家坐在一齊「老作」,但這個「老作」不單純是「老作」,我們心目中有些東西作為隱喻比喻香港,任何文明的起點都是一種隱喻,希臘文化起點是神話,不是甚麼奇怪的東西。
香港有很百厭、很「老作」的文化,不介意左偷右抄,需要時「老作」些東西出來也完全不會覺得內疚,尤其是香港電影,講食神,最後搞不定就弄個觀世音出來,搞定所有問題,我覺得好荒謬,只有香港人會這樣想事情,一套電影可以有日本漫畫、法國風格、荷里活元素放在一起,全不內疚極盡享受,就是這種無根精神。
無根精神是香港強項
何慶基:
有段時間我研究羅冠樵,他在國內畫的是抗日、救國,秉承中國傳統,其實那些畫好悶;訪問時他說要來到香港討生活才能完全從那些畫中解放出來。也斯亦很喜歡五、六十年代作家三蘇的文章。香港不屬於任何地方,沒有歷史使命,我們來香港為討兩餐,那種自由度釋放了好多東西。現在回看這無根狀態,在中國傳統裡是最大懲罰,所以人們常常批評香港,指我們是無根一族,但對我來說,香港文化的強項就是一種浮游狀態,一方面好像自己無從認同,另一方面是處於所謂的後現代社會,是一個好卓越的狀態。
我搞「盧亭」時好困惑,當時我是想通過這展覽挑戰博物館權威。那時藝術家創作了些古物,很搞笑的,我們找了個英國朋友裝扮成考古人員量地拍照,場內另有一個電視機,我們又找了個英國朋友,坐在書架後面說盧亭的發現如何重要。這些展品質素其實好差,完全看得穿的,但因為放在博物館的箱子內,就好像很有權威。當時有個父親跟女兒說:「我們的祖先就是用這些碗了。」我就覺得有點內疚;有些觀眾則覺得給作弄了,我又內疚,覺得自己好失敗。我其實希望他們見到歷史的含糊性,我最想呈現這個狀態,可能含糊性才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
梁文道:
我同意。當時找了陳育強參與,但他不太懂得「老作」,太認真了(笑),但我覺得有趣的是大家都關心所謂呈現的真實歷史,對於那些修辭我們都充滿疑問,無論是劇場人、文學人、做視覺藝術的人,大家都對甚麼是「真」的香港和歷史,都抱有懷疑。當時我們說本土的態度跟現在很不同,從前大家好想講,但都退一步,都很critical(批判),甚至cynical(犬儒),但現在沒有了,大家講本土都好肯定,「這個就是香港,你不是這樣就不是香港」,很嚴肅的,那時我們就比較playful(玩味)。
說回也斯的作品,他常常想告訴別人「香港不是這樣的」,那香港是怎樣呢?我也不知道啊。香港不是這樣又不是那樣,這樣講又太簡化,怎樣講才不簡化?應該怎樣講?他又講不出來,總是猶疑進退,不知如何啟齒,就是香港的狀態。那個時期大部分人都能了解這種狀態,香港幾乎是可以自己發明自己的一種人,自己創造自己。我們的歷史都有點虛假,我們的電影總是讓人覺得有種民族情懷,從李小龍到陳真到霍元甲到黃飛鴻到葉問,唯一共通點就是打鬼佬,幾十年來不變,香港人好像好愛國,但又好像不是,那種民族認同不屬台灣又不是大陸,而是「唐人」,是大陸台灣都不會再講的概念。我們這一班可以自己創造自己的人,永遠跟人做鬼臉,一講嚴肅的事就不知如何說起,卡在那裡,這些性質延伸到也斯的作品裡,日常生活當中不知如何抒解這種情緖時,不如就一起飲飲食食。
如《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就是給了我一個回憶,回歸當時真的很多飯局和派對。當時剛興起私房菜,大家吃飽了無無謂謂就喝酒,天天開派對,真有點紙醉金迷的感覺;透過食,可以講某些正經事,講香港歷史是怎樣,所有東西都可以連結到食,食可以解決到好多事情,可以解釋好多問題,是嗎?其實又不完全是。所以我都不知如何形容,那是一種很詭異的香港狀態。
九七的後現代與遊戲性
陳炳釗:
剛才提到那種浮游狀態,九十年代有個階段好強調「後現代」,強調那種遊戲性,我想起兩件事。一是也斯曾在《信報》寫過文章講劇場,是首個在香港介紹美國著名後現代劇團Wooster Group(伍斯特劇團)的作者。這劇團重新拆解經典,如老人演後生女,白人塗黑臉扮黑人,把那些錯置、現實和虛擬的東西放在一起,也斯好敏感,好喜歡這些東西。有趣的是,也斯亦很關懷本土,例如北角碼頭、本土食物,這些事情好實在好草根,但那種後現代的遊戲性,又可以說是很中產很無根,那個年代好多人都擁抱這兩種辯證關係。第二件事跟梁文道有關。好早期在「沙磚上」開會,他曾提議在香港某個山做戶外演出,要很認真寫新聞稿、開記者招待會、出海報,但那個演出是不會發生的,當時大家聽完這提議後都靜了幾秒(笑),當時你很樂意拋出這些點子。
九十年代那種想用一種玩的後現代方式去拆解香港歷史和狀況,另一方面會見到香港那種本土性,亦是我們想守住的,中間我們沒有答案,沒有排斥某些東西,但有一種極度想解放自我以及身邊所有人的狀況。我覺得這種狀態經過九七的轉折後 —— 後現代某程度上解決不到問題,遊戲性亦面對不了殘酷的現實 —— 千禧後就斷了,然後就只剩下本土性要面對,卻沒有了之前遊戲性的那種浮游,可以包容香港所有通俗文化的可能性,本土論述變得咬牙切齒,非常認真,甚麼是香港本土,甚麼不是,有一種界定、論述、對立的狀況,這是今天看現在的狀況跟九七當時狀況給我最大的感覺。
何慶基:
我覺得在1997年6月30日以前,我們有個假想敵,當時我們的信心強很多,「好啦我們來較量吧」,當時累積到一些東西,至少在視覺藝術界是累積到的。但回歸後我們原來想過的事情沒有發生,不是太壞,還好,有一點點變化;反而之前還有一樣東西一起去對抗,現在突然沒了對立面。過往中國在經濟上倚賴香港,現今是強國。香港卻不見得有甚麼特別發展,英國佬走了,中國我又不太認同,但我又是中國的一部分,應該如何定位?
這是自信的問題。九七前我們有危機感,但我們的創意和自信都很強,反而近年的本土化很沉重,當時我們可以接受自己的不足,講本土文化的過程可以自嘲。如跟也斯接觸時會感覺到香港文化特色,有時也可以講些嚴肅的事,但他不會跟你講完整哲學,東拉西扯的,這個是我最享受跟也斯在一起的時光,那種可以有深度,又隨時豁出去的態度。我覺得這就是香港的文化特色。
梁文道:
回想起來,我都好懷念過往的狀態。不過話說回來,剛才說的那班人,有少數例外,那時開始就在看不同的東西。如「進念」想的東西跟我們有些不同,對我影響也很大,榮念曾覺得香港如果繼續要有位置,不能不踏入大中華,要快點去大中華,所以他做《一桌兩椅》,踏進去搶個位置,否則就會消失不見,他是很認真去想這些事。現在回看我當然懷念當時的開放和好玩,肯自我嘲笑和批判的精神,不過我們那時全都欠缺對政治的切身感覺,當我們講九七,講後殖民,都是講文化講歷史,當時整個文化界很遠離政治,不切身。
當然我對現今本土的不同主張有很多保留,但回看我們當時這樣講本土化是有問題的,我們不夠實質地去看政治是甚麼。文化界對董建華的出現,沒有甚麼批判的角度,最多就是嘲笑他,但大家沒做甚麼就輕易接受他,當時文化界好少聯署做個聲明甚麼的去質疑他的認受性,我們沒人做這些事。為何我們當時如此apolitical(非政治)?我們講好多好大的概念:歷史、文化、身分,但全都不講政治。不知是否六四後遺症?當時在文化界和學術界,即使是研究後殖民的人都好少碰政治,這種政治貧血結果影響到今天。